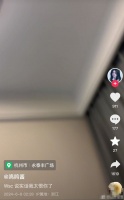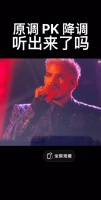黄永年诞辰百年︱石晓军:游子遥忆曲江春
引言
2025年10月24日是中国古文献学、中古文史研究大家黄永年先生(1925-2025)百年诞辰。为此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季活动,古籍整理研究所亦举办“纪念黄永年先生百年诞辰暨中国古文献学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日前黄先生高足周晓薇教授、王雪玲教授来信邀我也参加。我虽非黄先生的及门弟子,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曾有幸面聆先生所开设的相关课程,而且课余以及之后也曾与先生有过一些近距离的接触来往,承蒙先生提携赐教之处甚多。黄先生的教诲及熏陶,对我毕生的学习与工作影响至巨。每每念及,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藉先生百年纪念学术季之际,略忆昔日聆教等往事片段,以遥寄游子感恩缅怀之情。

黄永年先生
我大学本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1978年春季入学(高考恢复后的唯一例外),硕士研究生是81级,也是春季入学。记得初识黄先生好像是在春天,首次听黄先生课和近距离接触也都是始于春季。而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地处唐代曲江池的西北侧,我本科和研究生七年间的宿舍则坐落在今雁塔校区内“曲江流饮”池水之畔。因此只要提起黄先生,我总是会联想起曲江之春这一意象。故将这篇缅怀小文题为“游子遥忆曲江春”。
一、作为“唐史编外”听黄先生讲课
在我的记忆中,初识黄先生似乎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第一次听黄先生的课是在1981年春季大四第一学期。当时黄先生和牛致功先生给我们77级开设了“隋唐史研究专题”课程,记得黄先生讲课的内容似乎是有关唐前期政局相关的若干问题。当时我已在胡锡年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着手搜集本科毕业论文的资料,围绕明末清初朱舜水与江户时代的日本思想界的关系进行考察(其后这篇毕业论文以《朱舜水与德川光国的尊王思想》为题,刊载于《浙江学刊》)。由于主要精力都放在毕业论文上,所以我虽然也很认真地听了黄先生的课,但课余与黄先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记得当时全班同学好像都出席了黄先生的课。关于这一方面,同班同学吴萌著《素年锦时——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西安出版社,2024)一书中有记述(94-95页),可以参考。
我真正与黄先生的近距离接触也是始于春天,即1982年春季上硕士研究生以后。是年陕西师大历史系一共招收了六名硕士研究生(历史地理专业三人:费省、辛德勇、郭声波;唐史专业二人:黄新亚、齐永锋;中日关系史专业一人即我),其中只有我本科也是陕西师大历史系,其余五人都来自其他学校。六名研究生同学在雁塔校区的研究生宿舍(学生宿舍6号楼)二楼分住两个宿舍,历史地理三位住一室,我与唐史的两位同住一室,取《荀子·劝学》的“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之意,将宿舍命名曰“三驽堂”。 由于唐史专业的黄新亚、齐永锋两位师兄年长,尤其黄新亚兄颇为健谈,所以 “三驽堂”也就自然成为了历史系六名研究生的一个聚会沙龙,课余互相交流,天南海北,谈天说地。我对学校情况比较熟悉,早期则多充当学校“导游”的角色。六人不仅同住同吃(每天一起去食堂),还一同去上黄先生的课。
据辛德勇兄回忆说,历史地理专业三位同学上黄先生的课,是出于导师史念海先生之命。我去上黄先生的课,也是因为得到了导师胡锡年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因为胡先生希望我将硕士论文的主攻方向放在唐宋时期的中日关系方面。记得当时我先后选修了黄先生给唐史专业开设的“唐史史料学”“古籍版本及其鉴别”“古籍整理概论”等课程。由于每次都与唐史专业同学一起上黄先生的课,以至于同宿舍的黄新亚兄和齐永锋兄常戏称我为“唐史编外”。黄先生作为唐史专业导师,也不时会来我们“三驽堂”巡视指导,对我这个从本科就在师大历史系读书的“唐史编外”生也颇为关爱,亲自带来了上述各门课程的油印教材赐赠给我,令人感动不已。黄先生当时赠送给我的教材,我一直随身携带,珍藏至今。一看到这些四十多年前已经发黄的油印教材,眼前就立刻会浮现出黄先生授课时的音容笑貌。
二、黄先生的课对我的影响
听黄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每堂课都有不同的收获,令人钦佩不已。黄先生对史籍和史料的熟悉,逻辑严谨、明快的讲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中不仅可以感悟到先生博大精深的学养以及广阔的学术视野。还通过先生上课时的诸如“妙极了”“实在不敢恭维”等妙趣横生的表述,知道了一些在书本上很难了解的文史学界的掌故及动向等。选修黄先生的课,对我后来的学习和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仅就其中感触最深者略述一二,就我个人感觉而言,黄先生的课对我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下述两门课:
其一,唐史史料学。这门课程使我在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就有幸受到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一个系统训练,打下了比较好的基本功,初步具备了有关隋唐史料群的一些基本知识。通过这一方面的训练,为我之后从事隋唐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隋唐外交体系及外务官僚等研究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此外,黄先生分析史籍及史料的视野和方法,对于我考察研究整个中日文化交涉史也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成为我处理其他时代史籍史料时的一个指针。八十年代末黄先生的《唐史史料学》增订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后,我便马上又购藏了一本,常年置于座右参考。这一方面,是我首先想感谢黄先生的地方。
其二,古籍版本及其鉴别。这门课程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堪称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有机会跟黄先生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可谓三生有幸。在此之前,我本来就对版本目录之学有兴趣,本科时期自己也曾胡乱看过一些相关书籍,但始终有些云里雾里,不大得其要领。听了黄先生的课后,使我对此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线条。尤其是黄先生重点着眼于古籍的字体、版式、纸张这几大要素,对各个时代版本特征的概括及分析,令人豁然开朗。尽管当时并无条件接触实物,仅仅停留于书面知识。但这一学习经历却为我后来在日本关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整理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内藤文库古籍,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以前我没提及过这方面的情况,借此机会想稍微多说几句。
所谓内藤文库,即关西大学以近代日本东洋史学泰斗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1866-1934)的藏书为主,加之其父内藤十湾以及长子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内藤乾吉(1899-1978)的部分藏书而设立的文库。众所周知,内藤湖南不仅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奠基人和代表性学者,也是一位大藏书家。1926年内藤湖南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后,在京都南部的相乐郡瓶原村营建新居,因地近古代恭仁京而命名为“恭仁山庄”,故其藏书亦被称为“恭仁山庄本”。1983年秋,在关西大学法学部中国法制史学者奥村郁三教授(内藤乾吉的学生)的斡旋下,内藤家族将整个恭仁山庄一举转让给了关西大学。关西大学除了将恭仁山庄作为大学的教学研究设施之外,把内藤的全部藏书及手稿、遗墨、往来书简等,按照内藤湖南恭仁山庄书库排列原样,运至大学综合图书馆地下二层的电动密集书库内保存,命名为内藤文库。同时于次年(1984),由11位关西大学教授组成了内藤文库特别调查委员会,指导综合图书馆的馆员们开始进行具体的调查整理。
据当时的初步统计,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内藤文库共藏有典籍一万三千一百零五种,三万三千九百四十册。其中主要是中国古籍,以清代刊本居多,也包括一些明刊本、中国古抄本、日本古版本和古抄本、朝鲜本等。并有若干孤本。尽管内藤湖南生前曾将116种有关满蒙的文献给了京都帝国大学(现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文献中心),去世以后,其后人又曾于1938年将“恭仁山庄本”中的一些极品如被定为日本“国宝”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宋刊本《毛诗正义》单疏本、《史记集解》残本等一些罕见善本秘笈(计刊本67种、写本31种)转让给了位于大阪的武田制药公司(现藏武田制药公司下属的“杏雨书屋”)。但内藤湖南藏书的绝大部分则都收藏于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其中不乏珍本秘笈。此外再加上内藤湖南收藏的各种拓本、卷轴、手稿、往来书简等,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因而一举成为举世闻名的收藏内藤湖南文献的宝库。关于这一方面,可参见拙文《关西大学汉籍特藏简说》(载《第十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36页,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9年)。
调查整理内藤文库的最终目的是编写出内藤文库藏书目录。根据当时内藤文库特别调查委员会制定的编辑总方针,最终编写出来的内藤文库藏书目录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除了一般古籍著录的基本要素(书名、撰者、版本、刊年、版框等)之外,还需要著录序跋、印记、识语(尤其是内藤湖南的识语),以及调查该书在中日两国的其他已出古籍书目中的著录状况等。因此要求整理人员不仅要具备有关古籍版本目录的基本知识,还需要具有一定的书法篆刻素养。但由于当时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缺乏这方面的专职工作人员,而内藤文库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教授们也没有时间进行具体的整理编目,所以文库的整理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在我去关西大学之前,为了配合关西大学百年校庆活动,内藤文库特别调查委员会由奥村郁三教授率领博士研究生七野敏光等人,从内藤文库中选择乾隆以前的刊本及钞本1034种4530册,编纂了《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关西大学图书馆,1986年)。但该目录只是一个选目,其收录汉籍数量仅占内藤文库藏书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余大部分藏书都还有待于系统调查整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十年代初内藤文库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我的博士导师关西大学文学部大庭修教授(1927-2002)、藤善真澄教授(1934-2012)便推荐我去参与内藤文库的整理工作。于是,作为勤工俭学的一环,我一边准备博士论文,同时每星期都有几天去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书库,调查著录内藤文库的古籍。记得1993年下半年史念海先生到关西大学讲学时,我除了陪同史先生之外,其余时间则基本都在图书馆整理内藤文库。这一工作前后持续了大概三年,直至整理完所有线装书,我开始在关西大学兼课任教后才离开内藤文库。三十余年前我参与调查整理著录的那些内藤藏书,后来收录于内藤文库简目《関西大学所蔵内藤文庫リスト》№3(关西大学图书馆,1995年)、《関西大学所蔵内藤文庫リスト》№4(关西大学图书馆,1996年)。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内藤文库特别调查委员会原计划的详细目录,即包括藏书印记、藏家识语等在内的《内藤文库目录》至今仍未出版,衷心期待能早日问世。
当时我之所以敢接受这一工作,底气就来自以前在黄先生的“古籍版本及其鉴别”课上学到的一些入门知识。当时在我置于综合图书馆办公桌座右的几种参考书中,最重要的就是黄先生当年赠我的油印教材《古籍版本及其鉴别》(陕西师范大学,1982年版)。此外还有长泽规矩也的相关著作,以及已出的数种重要古籍目录。当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调查内藤文库的古籍的状态,著录各种典籍(主要是清刻本,也包括日本刊本、朝鲜本、以及一些古钞本),具体辨别其版本刊年、版框、过录藏书印记、藏家识语等,边干边学,通过具体观摩古籍实物,使我不仅对古籍版本学的相关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还初步了解了日本汉籍著录的历史与现状,前述拙稿《关西大学汉籍特藏简说》、以及拙稿《略论日本的汉籍著录》(《姬路独协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第17号,2004年3月,第1-20页)等就源自这一时期。我至今仍十分怀念这段难得的经历。每念及此,就由衷地感激黄先生。

《古籍版本及其鉴别》封面

《古籍版本及其鉴别》内页
三、黄先生赐给我的墨宝
除了听黄先生的课以外,课余也和黄先生有过一些近距离接触。受家父的影响(先父石心法先生工作之余爱好丹青篆刻,退休后入汉中书画协会、石门印社,并曾任陕西省老年书画协会理事),我自幼也喜欢绘画篆刻,“文革”期间闲暇较多,遂开始正式拜师系统学习素描、写生等,1977年12月参加高考之前还尝试报考过美术学院。1978年2月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以后,旋即成为陕西师大学生书画社的主要成员之一,经常参加以及组织一些书画展览等活动。因此我很早就略知黄先生在书法篆刻上的大名,十分钦佩。上研究生以后,曾去黄府求教相关问题,并因而结识了与我同庚的黄先生哲嗣黄寿成兄。其间应我所请,黄先生还曾赐给我一件墨宝。

黄永年先生书墙盘铭
黄先生赐给我的墨宝是一个金文条幅。内容是黄先生临西周《墙盘》铭文的开篇部分。
卷末行书署曰:“晓军雅属 永年临墙盘”其下钤印两方:“黄永年印”(白文方印) “心太平盦”(朱文方印)。
条幅上未署时间,具体年月我也记不太清了,在我的印象中,这幅墨宝似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黄先生所赐。当是黄先生存世不多的金文作品之一,弥足珍贵。
众所周知,《墙盘》亦称《史墙盘》,为西周共王时的史官墙所作的青铜礼器,故名。1976年12月15日出土于周原(今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白庄村)西周青铜器窖藏中,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据馆藏介绍说,《墙盘》为圆形,浅腹,圈足,双附耳。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盘腹饰鸟纹,圈足饰窃曲纹,盘底内有铭文18行,中间空一行,两边各9行,共284字。
铭文前半部分颂扬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诸王的功德与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史官墙所属的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迹。该铭文是1949年以后发现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由于其既记述了西周前期诸王的历史,也包括具体的家族史(微氏家族),堪称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史籍。其无论在青铜器断代,还是研究西周史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史料。同时作为西周中晚期金文书法成熟期的典型代表,在古文字书法研究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窃以为,黄先生以此赐我,或当含治史和书法两方面的勉励之意。
黄先生所书乃墙盘铭的前两行,计25字。其遒劲秀雅的笔法尽显黄先生的深厚的书法功力。随着《黄永年印存》(中华书局,2004年)的出版,黄先生独具一格的治印已享誉海内外,观此墨宝更可以了解到,黄先生超凡脱俗的篆刻艺术,其实正是建立在其精湛的金文等书法功底之上。关于这一方面,王其祎兄在《黄永年谈艺录》(中华书局,2014年)的《前言》中也有涉及,可一并参照之。
但这副墨宝上的两方印记却并非黄先生所刻。记得黄先生曾说过,名章“黄永年印”(白文方印)乃黄先生刚开始学习治印时的老师,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郭则豫先生(1890-1952)为其所刻;而闲章“心太平盦”(朱文方印)则是出自于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的著名篆刻家钱君匋先生(1907-1998)之手。为此我向黄寿成兄求证,寿成兄给了肯定的回答。如此说来,这幅墨宝不仅是黄先生的金文书法,实际还包括郭则豫先生和钱君匋先生的篆刻。
关于“心太平盦”,很多师友都已经讲过,此乃黄先生的堂号,黄寿成兄编著、辛德勇兄序《心太平盦古籍书影——黄永年先生收藏精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就是以此为书名。“心太平盦”的来历据说是黄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上海诵清阁书店“捡漏”购得罕见的明铜活字本《太平广记》,故以“心太平盦”来作为自己的堂号。如前所述,黄先生临书墙盘铭上的这方“心太平盦”(朱文方印)印章,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黄先生函请钱君匋先生刻后寄来的。其寓含“文革”中外界纷扰,我心却依然平静之意(参见曹旅宁《黄永年先生篆刻艺术趣闻》,载《收藏/拍卖》2014年第4期)。
黄先生手书的这幅《墙盘铭》,早已成为寒舍书斋的镇斋之宝。见其如见先生,衷心感谢黄先生的赐墨及勉励。
四、黄先生书桌前的藤椅
在这篇缅怀黄先生的小文准备收尾的时候,我无意中在网络上看见一篇来自微信公众号“芷蘭齋”的文章,题目为《书房/ 黄永年的心太平盦》(作者:韦力),该文卷首有一张图片,题曰“黄永年先生生前使用的书桌和藤椅”,是作者韦力先生2015年8月访问黄先生书房时拍摄的照片。

黄永年先生的书桌和藤椅
当看到这张照片时,我感到很眼熟也很亲切。不仅因为马上联想到了当年拜访黄先生时的一些情景,而且还由于照片中黄先生书桌前的这把藤椅,勾起了我早已淡忘了的一件往事。我老家在秦岭以南的汉中市。汉中气候温和湿润,风土人文和四川接近,出产各种藤器。记得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某年暑假,我回汉中看望父母时,黄先生曾托我代买过一把藤椅带回了西安。确切的时间以及如何从汉中带到了西安等具体过程等,现在都已经很模糊了,但对这件事情还有印象。而照片中黄先生书桌前的这把藤椅,从样子以及形制等来看,都很像是当年我买的那把。但是又一想,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恐怕那把椅子早就坏了吧?更何况照片中的藤椅看上去不像已经使用几十年的旧家具。但想来想去,最后我还是试探着向黄寿成兄询问了一下,结果寿成兄马上回答说,没错,照片里藤椅就是当年的那把。并且还说不仅黄先生生前一直在用,而且直至现在他去黄先生书房查阅文献等时,仍然还在继续使用。
听了寿成兄的回复,我既高兴又感动。高兴的是四十多年前买的这把藤椅竟能一直伴随着黄先生,我为之而感到喜悦和荣耀。感动的是黄先生竟如此爱惜身边的用具,一把藤椅使用数十年还宛如新品。但仔细一想,这其实也正是黄先生的一贯作风。黄先生任何时候都是衣冠整洁,一丝不苟,严于律己。无论对身边之物,还是对学校的公共财物,都是爱护备至,从不铺张浪费。关于这一方面,迄今有不少师友谈及,已成为陕西师大校园美谈之一。通过先生书房的这把藤椅,我再次对此有了深切的感受。
余言
以上所述往事,主要集中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八十年代前期尤其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1982年至1984年间,是我与黄先生来往最密切的一个时期。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1984年底我入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根据导师胡锡年先生和历史系领导的安排,1985年春开始在历史系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而彼时黄先生领导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则是独立建制,办公地点也与历史系不在一起。
在我赴日本留学之前,我在历史系一共执教近六年。其间除了代替之前在日本讲学时突发脑溢血而卧床不起的胡先生,给历史系高年级同学开设选修课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题课之外,还承担了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的基础课——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任务。随着刘念先教授的退休,我又被任命为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之前我一直以中古时期的中日关系史为主要研究领域,因此新的教学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世界近代史教学的压力很大,许多东西都需要重新学习,边学边教。记得当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自我充电学习,准备世界近代史课程教案上面。加之当时刚入职时,陕西师大教工宿舍紧张,我住在妻子工作单位的宿舍,离师大比较远,又有了孩子。因此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向黄先生请教的机会便逐渐少了起来,错过了不少请益求教的机会。至今思之,仍感到十分惋惜。
白驹过隙,一晃就是四十多年时间过去了。黄先生的音容笑貌及许多场景恍如昨日之事,鲜明地浮现在眼前,令人感慨万分。纸短情长,谨以这篇寄托游子仰慕怀念之情的追思小文,献给敬爱的黄永年先生。(合掌)
(2025年11月吉日石晓军草于东瀛白鹭城下往来斋)
相关知识
黄永年诞辰百年︱石晓军:游子遥忆曲江春
阿遥被阿奶质问,红豆被晓春质问,俩人竟都害羞了
方城县:百年接力传承非遗赏石艺术
“镌石永年——苏州碑刻技艺展”吴文化博物馆开展
认识王永年
"镌石永年——苏州碑刻技艺展"开幕 展石头上的史书
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
“越剧宗师”范瑞娟诞辰百年 业界传承发扬越剧精神
故乡百年特展忆金庸 当代“金迷”何以“笑傲江湖”?
“秋韵”(214) | 上游主题摄影征稿作品展——石春怀作品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54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596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0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45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19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