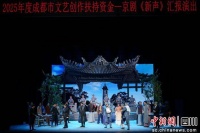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却写出名篇,字里全是家国大情怀

庆历六年的秋夜,邓州衙署的烛火格外晃眼。范仲淹捏着那封快马送来的信,指腹一遍遍摩挲着信纸边缘的折痕。
信是滕子京写的,那个和他同榜登科、共筑海堤的老兄弟。信里说岳州的岳阳楼修好了,想请他写篇记。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卷《洞庭晚秋图》。
他展开画卷,墨色的湖山在烛光下晕开。其实吧,范仲淹这辈子从没去过岳州,更没见过真正的洞庭湖。可看着画里 “波撼岳阳城” 的气象,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泰州的日子。
那时他主持修捍海堤,滕子京主动来帮忙。寒冬腊月里,两人踩着冻土勘察,冻裂的手互相呵着气,都说要让百姓再不受潮水之苦。后来那堤叫 “范公堤”,可范仲淹总记得,滕子京熬红的眼睛比堤上的灯笼还亮。
二
这几年的境遇,真是一言难尽。庆历新政刚铺开摊子,就被守旧派搅得稀碎。他从副宰相贬到邠州,又转任邓州,成了朝廷眼里的 “逐臣”。
滕子京比他更惨,遭人诬陷贬到岳州。换旁人早消沉了,可这老伙计偏不。信里说岳州如今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字里行间全是不服输的劲儿。
范仲淹对着画卷发怔,索性起身走到花洲书院。月光洒在新栽的柏树上,树影晃得人心里发沉。他想起在陕西御敌西夏时,滕子京守泾州,每次送军情来,信末总不忘问一句 “百姓安否”。
那一刻,画里的洞庭湖忽然活了。那些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的景象,不就是朝堂上的明枪暗箭吗?那些 “忧谗畏讥,满目萧然” 的感触,早刻进了每个被贬官员的骨头里。
他忽然明白,滕子京要的不是一篇普通的游记。这老兄弟是懂他的,知道只有他能写出那种藏在山水里的委屈与坚守。
三
笔墨早就备好了,是滕子京特意托人捎来的徽墨。范仲淹提笔时,手竟没抖。
他没写岳阳楼的雕梁画栋,也没写洞庭湖的四时之景。他写的是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写给滕子京的,也是写给自己的。官场上的沉浮算什么?只要心里的信念不倒,就不算真的输。
写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时,他停了笔。窗外的秋虫叫得正急,像极了那些在民间嗷嗷待哺的百姓。真的,真的不是他想唱高调,为官一任,若不能为百姓做点实事,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庆历新政失败后,他夜里常睡不着,总想着那些没推行下去的利民政策。可此刻对着画卷,所有的焦虑忽然有了出口。他笔下的洞庭湖,早成了天下人的江湖;他写的岳阳楼,也成了每个志士心中的坐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十四个字落纸时,烛火 “噼啪” 响了一声。范仲淹望着纸上的字迹,忽然笑了。他好像看见滕子京收到文章时的模样,说不定会拍着桌子喊 “知我者希文也”。
四
后来岳阳楼成了天下名楼,人人都夸范仲淹写得好。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到死都没踏足过岳州。
有人说他是 “纸上谈兵”,靠一幅画瞎写。可只有真正懂的人才明白,好文章从来不是靠眼睛看的,是靠心去悟的。那些藏在文字里的家国情怀,早在泰州的海堤上、陕西的烽火里、邓州的月光下,熬成了最浓的底色。
去年我去岳阳楼,站在 “先忧后乐” 的匾额下,忽然想起范仲淹那夜的心境。楼外的洞庭湖浩浩荡荡,风一吹,好像还能听见千年前的笔墨声。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有些没去过的地方,反而能看得更清楚。就像范仲淹,他没见过岳阳楼的模样,却写出了它最该有的灵魂。这种灵魂,藏在每个心怀天下的中国人骨子里,从来没变过。
相关知识
岳阳楼的千古风华与文化传承
范仲淹写一首相思名篇,李清照模仿最后三句,结果成了传世经典
安吉丽娜·朱莉一次Met Gala没去过,红毯造型却出圈无数…
读懂范仲淹《岳阳楼记》我顿悟:没有一种人生不辛苦,熬过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若觉人生太迷茫,劝君重读《岳阳楼记》
这个家还得靠大姑姐,酒窖里居然全是金条
人文齐鲁|范仲淹的“楚丘”情缘
《世界在走,我坐着》:文字里的家国情怀
灾民买不起米,范仲淹却下令再涨价一倍,专家:此举救了百万灾民
范仲淹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08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551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774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564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637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684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36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071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054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