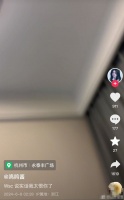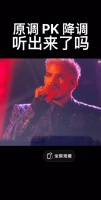【王蒙文学院•环渤海文化】孙 郁丨王蒙与俄苏文学的几个问题
2024-12-16 09:05
辽宁省 (第6052)总编 | 觉 澜 || 主编 | 亓 雪


文艺争鸣
推送《文艺争鸣》所刊发的优秀学术文章。
一
中国人对于俄国一直有着复杂的情感,其中因由,一时难以道尽。有几个时期,俄国的文学是颇吸引了国人的注意的。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这个邻国的资源一直蕴含其中。谁都知道,20世纪的俄苏文学翻译十分活跃,二三十年代俄苏文学翻译数量大增,50年代初达到高潮。而这两个时期,恰是文学思潮变动的阶段,知识人的思想风貌也出现新的变化。王蒙曾经感叹:“俄罗斯的文学太沉重太悲哀太激情也太伟大太发达了”。这种感叹与30年代左翼作家不无相同之处。讨论这个话题,他与鲁迅那代人都提供了丰富的阅读经验,从几代作家的摄取域外审美意识的过程,也看出新文学发展的轨迹,中国知识人如何借外来思想解决内部问题,他们身上呈现的意象,都有代表性的意义。
鲁迅那代人翻译介绍俄苏文学,存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拷问和精神自新的问题。即如何从旧的营垒进入新的精神天地,并将且改良人生纳入实践中去。那些作品“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颇有参考意义。王蒙那代人与俄苏文学相遇,则是走进革命,且在大的爱意里描绘出精神的狂欢。鲁迅将自己视为革命的同路人,而王蒙则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前者要处理传统带来的重负,后者则沐浴在列宁主义的阳光下,在空白处描绘最新的图画。
同样是接触俄苏文学观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观念,鲁迅没有进入列宁主义世界,还停留在普列汉诺夫和早期的卢那察尔斯基的阶段。但王蒙是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语境开始自己的审美历程的。这种差异也导致了写作姿态和视野的不同。鲁迅自身的个人主义痕迹依稀可见,而王蒙是革命队伍里的先锋派。这先锋派不是亚历山大·雅各武莱夫和康斯坦丁·费定式的,而是伊萨克·巴别尔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式的。鲁迅最早提及过巴别尔的成就,但并不了解深层的轨迹如何形成。但王蒙是深入巴别尔那代人的世界的,知道革命者也可以在精神游离中超越世俗的感觉阈限,向着陌生的极限挺进。我觉得从这种差异性里认识从鲁迅到王蒙的创作生涯,当明了文学史特别的一幕,中国新文学何以走上后来的路径,他们提供的经验都是值得深入打量的。
在俄苏文学遗产里,理论家的文本不如作家的文本提供的东西多。鲁迅与后来的王蒙对于这个斯拉夫民族的艺术的摄取,主要是文学文本,理论文本还在其次。俄苏文学的复杂性,鲁迅一开始是朦胧地意识到了,而王蒙后来经历了认知的正反合过程。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读者还不太了解斯大林时代之后的苏联文学形态的变化,像格罗斯曼、布罗茨基、曼德施塔姆等作家,介绍得不多。而人们耳熟能详的是西蒙诺夫、波列沃依、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待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读书界对于俄苏文学的历史,才渐渐明了起来。回望以往,无论对于鲁迅这代人还是王蒙这代人,他们对于俄苏文学的趣味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那些确切性的元素,而是那些矛盾的,带着智性穿行于时空中的精神冒险和思想的达成方式,那些飘忽不定而神异的存在,却真的将人从凝固的世界中剥离开来,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提升。
俄苏文学提供的不都是答案,而是一系列存在于灰暗中的各种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和面对问题,对于中国作家而言,也是对于自我的发现和自我的提问。俄语里埋藏着许多智慧的表达式,像“伊索式语言”“审美乌托邦”“弥赛亚精神”,都为汉语书写的格式中所少见。五四之后的汉语表达在丰富自身的时候,注意到对于这种异质的审美韵致吸收的重要性。它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一时过于其他民族的文学,这在文学接受史中,是极为特别的现象。中国知识人在增益知识与思想的过程与外来资源的对话与互动,经验的春色中也未尝没有遇到寒意。如今遥望以往的历史,今人的感受也不免五味杂陈。
二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王蒙属于老北京,但他既非京派作家,也非京味儿文人,常常是游离于古都的历史。他好奇于域外文学,很早就被苏联的一切所吸引。那里的不安的、飘逸的神色托起一个突奔的梦,自己完全被淹没于其中。他幼小时期就有意识拉开与古文脉的距离,对于帝京的文化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城门外的世界引导着他的目光,他似乎觉得,京派的自由主义似乎过于暮气,而京味儿又太世俗化了。这些都无法给自己的精神带来愉悦。现代性不是温情脉脉的花香鸟语,还有摧枯拉朽的风暴,后者对于他,乃自由的象征。于是在叛逆与激情中,有了别开生面的渴念,在稚气的文字里开始苦苦地寻找另一类的人们。
那些来自斯拉夫的声音给他以无限的神往,无论是柴可夫斯基还是肖斯塔科维奇,不管是普希金还是格拉特珂夫,都给予他想象的空间,早期作品含有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外在的排他性与内在的丰富性是俄苏文学吸引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是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他早期写下的《青春万岁》里可以清晰看到其思想本色。不过在追求精神的纯粹性过程中,他很快遇到了生活的混沌性,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革命政权内部生活的片段,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在复杂的机关里感受到了异样的人生,失望的情绪是浓烈的。但在压抑之中,依然感受到了理想之光。这些无疑受到了苏联文学的启示。于是我们在他的作品看到了柴可夫斯基式的摇曳感,词语里带出特瓦尔多夫斯基式抒情特点。他后来谈到自己喜欢俄苏文学的原因时写道:
他们承认人道主义,承认人性、人情,乃至强调人的重要、人的价值;而中国的文学理论长久以来是闻人而疑,闻人而惊而怒。二、他们承认爱情的美丽,乃至一定程度上承认婚外恋的可能(虽然他们也主张理性的自制),并一定程度上承认性的地位。三、他们喜欢表现人的内心,他们努力塑造苏维埃的美丽丰富的精神世界。而在中国,长期以来文艺界相信“上升的阶级面向世界,没落的阶级面向内心的断言”……
即便在特殊的年代里,王蒙对于苏联的文化形态依然是抱有兴趣的。《狂欢的季节》里这样写主人公在新疆边界中的感想,对于已经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国度,有着别样的心解:
那边至少还可以跳华尔兹舞,可以写爱情诗,可以在抒情歌曲里歌唱姑娘房间里不灭的灯光。那边的电影里也有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有大海,有街头花园的簇簇鲜花,有漂亮的男女青年述说他们对幸福的向往。而我们这里的一切有趣味的有生活的有美感的有灵气的东西全都成了革命的死敌。
苏联是否属于修正主义且不说,它在艺术层面带来的光泽,是中国文学要汲取的。所以在小说中,不时出现联共(布)党史的话题、托派遗产、斯大林主义等气息,都萦绕在其间。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以及《青年近卫军》等片段交织在主人公的思绪里。革命与富有想象力的诗文交织在一起,诞生的是浪漫的高蹈。王蒙的精神就在这个浪漫中被沐浴着,那种空旷中的幽思,与天地悄悄对话的神情,某些地方让人想起屠格涅夫和肖洛霍夫的文字里的颜色,冲荡中的辽远之气,将精神引向神异的地方。
苏联解体无疑给王蒙很大的震动。疑惑与追问在其作品中偶有表述。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是以苏联友谊为题材的,从对于苏联艺术的崇拜,到中苏合作的蜜月,再到两国交恶后的沧桑,以及苏联解体的感受,冷战及冷战结束后的东方政治版图的演绎,映衬着思想与审美的纠葛之痛。审美里的政治,不是政治中的审美,王蒙和鲁迅一样,在创作上以前者为提要展开自己的写作,但他们却共同遇见了政治中的审美戒律。在鲁迅那里是以抵抗周扬的压抑而保持野性,而在王蒙那里,则选择了杂色,即于理想中警惕着什么,在困境中憧憬着什么。而这种憧憬不是回到陶渊明那里,而是瞭望没有路的前方,突围的热情弥散其间。
俄苏文学的参照,使王蒙的创作出现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空间的辽阔性,不仅仅凝视东方经验,也吸收中亚与东欧的精神资源。二是人性表达的复杂性,在时间纵轴里,刻出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他的《蝴蝶》《杂色》《布礼》《活动变人形》及“季节系列”的作品,都记录了时代的坎坷路途,政治与文化、民俗与士风、人性与民族性等,杂糅于一体。我们可以将此视为自我经验的一种提纯,主人公既在革命的风云内部,也神游于风暴的外部。拷问中的深思和理解中的释然,在酣畅淋漓的笔致中得以升华。
在王蒙那里,五四那代人对于现代性的渴念,是被延伸为革命性的路径中的,胡适提倡的写实的感受,被他转变为先锋性的体验。革命与先锋是同义语。马雅科夫斯基、勃洛克都描述了革命,然而他们都是俄语世界的前卫性的人物,词语的逻辑被不断改写,精神的坐标被位移了。鲁迅当年介绍的苏联艺术家,都不在古老的传统里,带有精神的突围性,在鲁迅看来,革命者也是审美的前卫战士,毕斯凯莱夫、法复尔斯基、毕珂夫无不如此。不过王蒙与鲁迅不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忧郁与灰暗,而含有艾特玛托夫式的宏阔与激昂。不是安德莱夫式的阴冷,而是伊萨克·巴别尔式的轰鸣。他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的词语实验,就颠覆了京派式的儒雅和来自苏区文学的肃穆感,而是在反讽、归谬、深省、回旋中画出旧岁风貌,一代人的风风雨雨,沧桑之气,都于此生动地流动出来。这个时候读者会联想起潘诺娃《光明的河岸》,爱伦堡的《解冻》,以及格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与鲁迅那代人比,传统的阴影被切割到历史的沟壑里,王蒙在文本世界里的洒脱与逍遥,是前辈作家中很少见到的。
三
用俄苏文学的方式矫正中国文学创作问题,或许是王蒙的深层动机。比如人性化的展示,内省性,崇高感等,无一不可借鉴。自从胡风文学观受阻后,文学的功能被日趋窄化,有灵气的作品日见其少。王蒙从苏联作品中看到生机勃勃的一面,那里是阴晴俱在,苦乐悉存的。《士敏土》就不回避主人翁缺点,人的七情六欲在故事里是晃动的。《静静的顿河》也非一种声音,在轰鸣里高低互存,昏暗里见到明亮之色。革命题材不是过滤杂质,而是呈现着杂质里的纯真如何可能。《毁灭》写了莱奋生的迟疑与不安,《青年近卫军》里的战士色泽各异。至于同路人作品中颓败感的流泻,无望里的凄冷,都一定程度表现了精神的真。在巨变时代,旧的必将过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路翎之后,中国小说家一段时间不易见到《财主底儿女们》那样撕裂性的审美表达,这种态势使王蒙感到不满。我们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结构,就有矫正以往左翼文学的叙述用意。
王蒙对于苏联作家抱有敬意者甚多,其中伊萨克·巴别尔是其中一员。巴别尔《敖德萨故事》属于早期记忆的描述,混沌与庄严、残酷与温柔那么复杂地交错其间。《骑兵军》对于“逻辑怪圈”的拆卸,奇思迭起。这种在凌乱与死灭里展示人性光泽的作品,我们在王蒙《杂色》与《活动变人形》中亦可看到。王氏的复杂性不是卡夫卡式的,与黑塞的那种哲学意味的表达也有所不同,这些主要来自俄苏文学的馈赠。巴别尔与高尔基的交流,以及在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工作经验,与他的作品的蒙太奇式的与核爆炸式的精神辐射,给世人的惊异至今没有消失。王蒙的写作同样是带有繁复、冲荡与不可思议的悖谬之曲。他的纯然的感受是在扭曲与变异中猛烈生长出来的。
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概念描述王蒙的精神选择。上面我们谈到王蒙的开阔性与复杂性,是研究其内在精神不能不考虑的元素。他在《淡灰色的眼珠》中描绘的伊犁故事,就是多种民族、多种记忆、多种撕裂的政治语态的交响。主人公马尔克木匠的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汉人,属于“黄胡子”,“据说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难民,被侵华日军打散,从海参崴、伯力一带逃亡到苏联境内,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苏联的中亚,从阿拉木图一带回到我国新疆伊犁地区的”。作为一个混血儿,马尔克血液里也有近代史的悲凉元素。他在伊犁的生活传奇而感人,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以自己的智慧与不幸的命运周旋。在他身上几乎集结了时光里最为曲折的人影,但这种描写不是抽象的,人物的特别有时候让我们想起《敖德萨故事》的某些意象。这里已经看不到丁玲式的单线条的画面,也无巴金那种线性因果,但通篇的沧桑感和悲悯,则带着肖洛霍夫式的回旋之力。那时候的共和国小说几乎没有这种类型,王蒙的富有锐气性的表述,给文坛注入的热流实在是令人难忘的。
四
鲁迅限于环境,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苏联的误读,王蒙在1983年访苏时便开始反省自己的俄苏文学观。他在苏联解体后,对于历史的反省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非新左派的,而是带着清醒的现实态度和沉重的历史感。这一点使他与同代许多人发生了分歧,但也拥有了共同的交叉点。在李泽厚那里是回到康德主义中去,巴金则重提托尔斯泰主义,而王蒙却带着布尔什维克之迹,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并且借鉴老庄、孔子的思想,在中国智慧里调试自己的人生观与审美观。苏联解体后,如何看待其文化遗产与艺术遗产,是有过争议的。王蒙在1993年发表的《苏联文学的光明梦》,就带出复杂的感受,既不是欢呼,也非哀叹,以反流行的看法,对于自己钟爱过的苏联发出诸多感慨。我一直觉得20世纪90年代是王蒙文学观念的转型期,他对于文学与政治、审美与伦理的认知,较之80年代略有调整。这调整的原因是,不再仅仅以苏俄文学作为参照辨析社会问题,而是从古代遗产和现代非左翼遗产中汲取智慧和养分。在纷纭多样的文学传统里,他对于俄苏文学的基本问题有了清晰的图案。这一切反映在对于日丹诺夫、周扬、丁玲的看法上。
《想起了日丹诺夫》是王蒙一篇重要的反省性的文章,也看出作者对于红色文学的基本态度。在这篇文章里,王蒙意识到了俄苏文学传统内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向被文坛所忽略。无论是周扬还是胡乔木,言及俄苏文学经验,都回避了其间的内在性的问题。自托洛茨基成为讳莫如深的名字后,艺术与政治之关系,在文坛是被简化地表达的。而实际上,苏联文学一直有着不同思潮的内卷,作家协会中的风云涌动,作家个性很少是统一过的。俄罗斯文学曾经历过对于上帝的崇拜到对人民崇拜的过程,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斗争也没有消停过。而关于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之关系的思考,也一直处于一种探索和未完成的状态。1946年之后,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的写作就受到了严厉批评,以为是“异己和有害的现象”。日丹诺夫对于苏联的个性鲜明的作家的批判,带有某些唯道德主义的倾向。不过,在批评界,人们并非都同意日丹诺夫的思想。1972年,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出版。在这本书里,思想已经有所开放,作者写道:
不能够把历史决定论理解为外部的、局外的力量的不可改变的强制;历史决定论不仅不跟创作自由、创作探索发生矛盾,而且还必须以创作自由和创作探索作为社会的、艺术的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十多年后的王蒙的关于文学的思考,与赫拉普钦科显得极为接近。他们都关注风格的独一性、表达的深切性,并且在一种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语境里考察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赫拉普钦科的著作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审美意识是敞开的,没有日丹诺夫的狭隘之气。他十分熟悉卢卡奇、萨特、荣格和海德格尔的学说,并一再强调“自己的声音”的重要性。失去个性的作家,是孱弱的。这种态度也恰是王蒙对于文学写作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俄苏的文学资源的摄取,是灵活而不僵化的,而且学到了那些灵动而带有独创性的东西。在谈到日丹诺夫的文学观念的时候,王蒙叹道:
读一读日丹诺夫的讲话,真可以说作是义正词严、浩然正气、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了治了。他坚持自己代表的是真理正义光明,而自己所否定的是反动腐朽黑暗。这种绝对化思维模式实在是危害太大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王蒙对于俄苏文学一直存在的批判意识持肯定的态度。在创作中所礼赞过的作家,多少都有一点直面黑暗的勇气。而他肯定丁玲、巴金的作品,也是因为其间的俄苏传统的猛烈之气的流转。王蒙由日丹诺夫联想起特殊年代中的极“左”思维,由此意识到苏联文学遗产的复杂性里,也映照出中国文学的复杂性与缠绕性。他对于王朔、莫言的不合时宜的某些作品的欣赏,都说明对于极“左”的话语已经具有了某些免疫力。由此而反观自己年轻时代对于苏联文学的单纯的礼赞,是模糊了诸多事物的界限,对于未知事物的盲目性思维,也不是没有的。当他谈论周杨前后变化的时候,或许也会联系起自己。而有个时期,周扬晚年式的表现,也是被他继承下来的。从他对于周扬、丁玲的印象里看,他们生命中最为可爱的部分,恰是脱离日丹诺夫影子的时候出现的,俄苏文学美丽得过于残酷,如果只有残酷,失去美丽,思想就枯萎了。
五
晚年的王蒙接触过许多新京派的作家与学者。季羡林、张中行、汪曾祺、宗璞等人的知识结构都缺少苏俄元素,但他们真正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思潮。这些使王蒙不能置身于外,他开始思考那些曾被遗漏的遗存,从中填补自己的意识空白。比如,他对于张中行某些观念的欣赏,但却无苦雨斋辞章的安宁。他对于王小波的批判性思维是认可的,而罗素式的哲学在他那里并不显得十分重要。京派的特点是对于俄苏文化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多有批判。王蒙后来虽然对于新京派表示过某种敬意,但对于心中的苏联的乌托邦之意带给自己的美好记忆,并未弃之身后,而是感激那狂欢的季节迸发的生命的热能。不过,他对于王小波的理性主义是认可的,因为怀疑主义的科学精神殊为重要。王蒙晚年欣赏的许多人与事,都是偏离斯拉夫语境的,诸多作家对于俄苏文学的审美的消解,对于他自己未尝没有深的影响力。但要动摇生命中的乌托邦精神,似乎也是难的。
新京派的出现,对于知识界的影响,渐渐超出王蒙、张贤亮、李国文这批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作家,那原因十分复杂。汪曾祺、张中行、宗璞、阿城、王小波等人的知识结构,俄苏的元素是被稀释掉的。他们在冷静的文字中,关注的是世俗社会,而非左派的激情。从汪曾祺、张中行、王小波文章里,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苏联文化逻辑的漠视,审美的路向是回到自由主义语境的。而一些青年批评家对于王蒙的批评,可能也基于相似的立场。新京派的作家与批评家不再关注溅血的革命,而是日常生活,比如风俗、语言、图腾,西方语文学家的素养开始置换东方单一的道德话语,其特点不再是宏大叙事,而是回到没有体系的体系。在这里,革命与世俗精神是对立的,后者似乎更被人们所玩味。但王蒙并不同意类似的看法,他常常努力协调那些看似对立的元素在精神结构中的位置。他认为,“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三者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革命者和精英们理解人民大众的正当世俗愿望,并为满足人民的这种要求而努力而献身,实在无伤于革命和精英,而正是革命与精英之所以为革命与精英的题中应有之义”。
晚年的王蒙对于西方各种文化传统的认识增多,看到了俄苏之外的传统的时候,意识到民族性与独创性的重要。而摄取域外经验,建立立体的认知感受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他到印度就感受到泰戈尔的另一种意义,“泰翁曾经被自己所属的种姓与阶级所咒骂,然而他也从中获得了人民性,获得了人民的感情与赞扬”。访问德国的时候,才知道战后德国何以少说爱国主义,因为希特勒曾经玷污了这个词语,将爱国引向了另一个方向。在游历伊朗的日子里,发现了对于现代化的另一种理解,宗教与艺术的隐含忽地明了了许多。显然,这些多少都影响了他晚年的写作,背后的资源也变得多样化起来。
但早期记忆给他的印象毕竟是不可抹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喜欢谈论俄苏的作家的,只是角度与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界大为不同。90年代之后,关于个性主义的作家的译介依然活跃,人们把目光更多集中在那些逆俗性的文本里。这时,王蒙与青年一代的差异也就显示出来。较之于知识界对于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的趣味,王蒙更关注法捷耶夫、巴别尔等遗产在今天的价值,并把不同遗产的元素重新组合起来,甚至也注意到汪曾祺的价值,那么说他与新京派有对话的关系也是对的。这里,王蒙从有激情的歌咏到冷静的自我思考,知道尊重常识与理性的意义,知识界不能没有智性与趣味。当回到智性与趣味时,唯道德主义的审美就与他很远了。从纯粹到杂色的过程,也就是思想不断生长的过程,他也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精神蜕变。他的复杂性也恰在这里,不再是武断主义、一元论和排他意识,一直在质疑、反省、拷问里丰富自己。这种状态,有对于既有的观念的坚守,也有记忆的修正。先验的观念不能都开花结果,寻路者才会在拓展中“转识成智”“达于大道”。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之梦,受益于他那代人的启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蝴蝶》《杂色》《十字架上》《一嚏千娇》都是跨越樊篱的文本。七十余年的苍茫之路,因为有了这些存在,使我们知道,如何在不确定性里保持自己的确定性,写作者不是为了先验的概念而存在,而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把人置入存在之敞开状态中”。在敞开的天地里,人才懂得了什么是自由和不自由。
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1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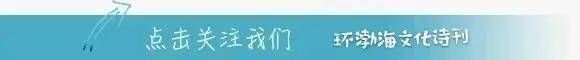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新时代与新的文学”主题论坛举办
90岁王蒙:写作仍要变法求新
三位青年作家入选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丨十月文学月
文化大家王蒙与陕西作家见面座谈会在西安举行
“青年文学需要提供新的审美方式” 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特选名单出炉
90岁王蒙从事文学创作70年,2000万字《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出版
王蒙文学创作70年座谈会暨《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发布会在京举办
三位青年作家入选“王蒙计划”
从听王蒙讲“春天一堂课”开始
“人民艺术家”王蒙为黑龙江文学馆“文学周末”题字
推荐资讯
- 1李沁肖战已同居领证? 李沁肖 49250
- 2闫妮老公邹伟平简历 闫妮前 44666
- 3王凯蒋欣承认已有一子? 结 40852
- 4王灿前夫 王灿的第一任老公 36603
- 5汪希玥回北京过年,怎料见到汪 32711
- 6霍启山与霍启仁对嫂子郭晶晶的 29740
- 7张佳宁和宋轶长得像 同属甜美 25784
- 8央视主持孙小梅丈夫曝光,是大 21156
- 960年代,洪秀柱(右后)与父 20127
- 10佟丽娅事件是什么 佟丽娅回应 19527